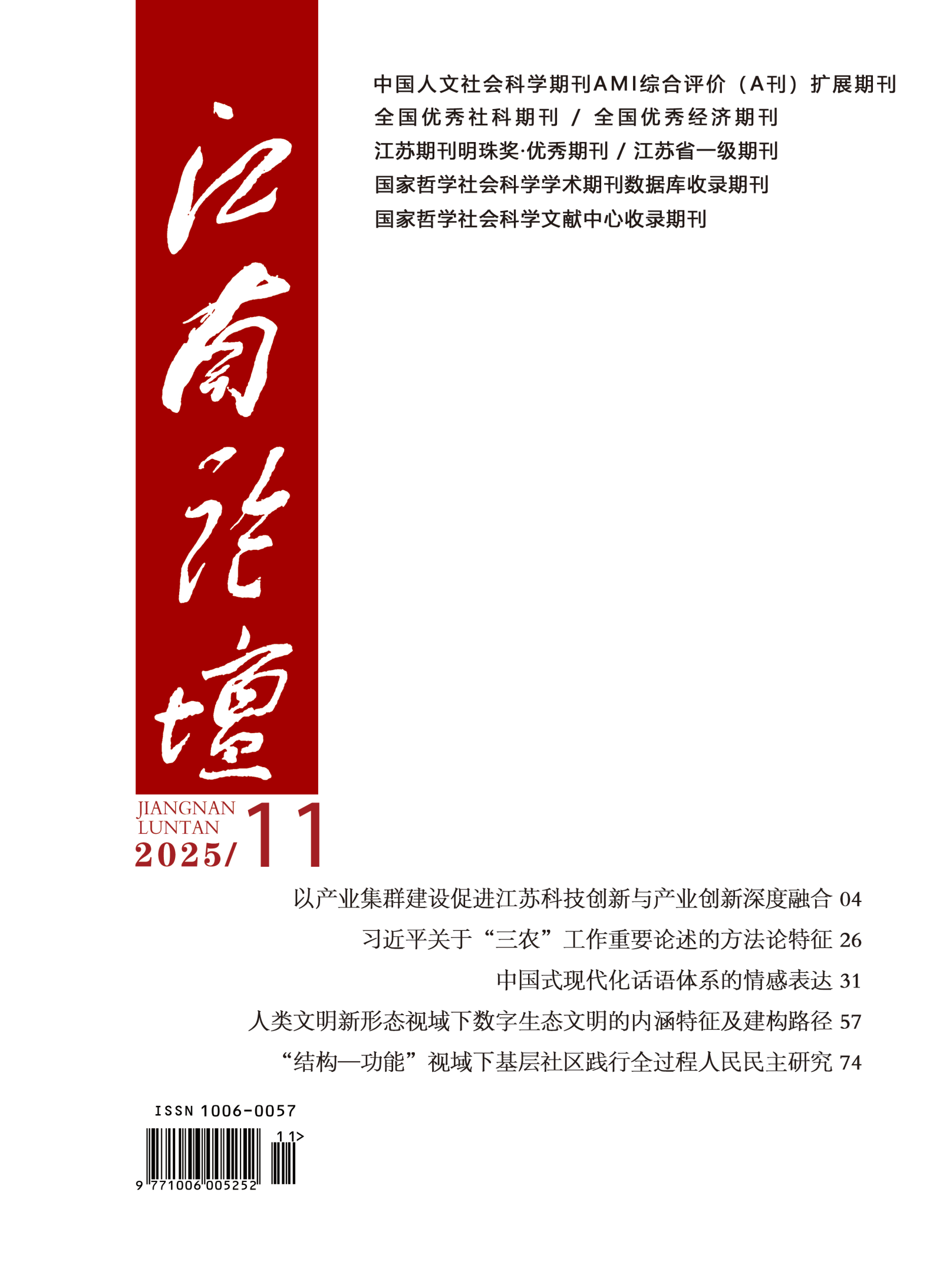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话语叙事、内涵要旨与世界意义
摘 要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一个包含“话语主体—话语场域—话语载体”的复合型话语结构,分别指涉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三个话语要素。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魂脉”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滋养和西方现代优秀文明成果的“对话”交融。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体现了对世界文明发展图景的深切关怀,通过“重塑发展模式—构建发展空间—创新发展形态”三维文明发展路径,为打破“西式文明”中心范式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促进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注入了中国力量,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了中国贡献。
关键词 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
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既是中华文明自身发展演进的必然逻辑,又是对当今时代如何布展文化建设的应然回应。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1]从“中华文明”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呈现出怎样的话语叙事转变?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交织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具备何种内涵要旨?在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交流碰撞的情势下,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应如何跨越全球文明发展藩篱,彰显更为宏阔的世界情怀?深入剖析上述“文明之问”,对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话语叙事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一个复合型话语结构,包含话语主体、话语场域、话语载体三重话语要素。彰显突出连续性的“中华文明”构成了叙事主体,体现了话语的主体性;纵深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形塑了叙事场域,明确了话语的在场性;繁荣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织就了叙事载体,凸显了话语的具象性。
(一)话语主体:彰显突出连续性的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主体确认问题是把握中华文明形态演变和发展脉络的元问题。“中华文明”由“中华”和“文明”两个独立的话语范畴组成。“中华”既是一个地缘概念,也是一种独特的文明现象。“文明”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一般具有教育昌明、道德开化之意。如《尚书·虞书·舜典》有言,“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意为智慧而德高,文明且恭敬。“中华”与“文明”并育组构的“中华文明”不是术语间的机械镶嵌和简单叠加,而是话语叙事的进阶拓展和意涵丰富。“中华文明”不仅旨在表征中华民族基于地缘要素所缔结的整体性、共同性,更凸显了特定文化背景下民族文明的连续性、认同性。由此,“中华文明”一词以其广阔的历史纵深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使“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有了明确的身份确证和主体归宿。
从现代转型视角审视中华文明的演进脉络,本质上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连续性的客观承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2]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图谱中拥有闪亮的时空坐标。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3]中华文明正继往开来,循着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不断拓宽发展之路。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所生成的“现代”样态。“连续性”的所指并不是线性时间的单一流变,而是历史“规律性”的科学总结与正确展开。只有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持续推进“面向未来”的创新创造,才能使文明演进更加契合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从“中华文明”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变的是话语表述的丰富拓展,不变的是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历史初心。作为话语叙事的主体范畴,彰显突出连续性的“中华文明”从根本上锚定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主体旨归与发展进路。
(二)话语场域:纵深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文明形态的演变不是虚浮的抽象过程,一旦悬置于特定的发展场域外便无法呈现和彰显。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为理解“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话语生成场域提供了一个恰切的分析视角。布迪厄将“场域”描述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4]按照他的理解,场域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场域可以指代一个特定的社会关系空间,各种关系相互联系或链接,进而构成复杂的关系网络;二是场域内部存在各种力量的相互博弈,能够反映诸多关系的演变历程和发展规律。基于场域的二元特征,观察和理解“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这一重大文明发展事实,必须将其放诸特定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之内才能充分把握文明发展的科学动向。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作为中华文明的“现在进行时”,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存在密切的逻辑关联。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提供不断形塑发展的动力与空间;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为衡量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效确立了文明维度的内在标尺。
中国式现代化既开创了道路样式,又推进了文化创造。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深切呼应了中国式现代化新文化形态创造的必然要求。首先,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理论内容生发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由实践检验得出的文明发展经验又反过来指导现代化实践,这种“理论—实践”双向互动的文明演进链条构成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进步基因。其次,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模块,而是共同组成了能够完整呈现文明发展壮阔图景的重要拼图。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包含了要求中华文明进行现代转型的文明发展诉求,且现代化实践还深刻影响着现代文明的最终面相。最后,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文明发展叙事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性叙事经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复兴叙事得以有机统合起来。在此意义上,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便不只是单向度的文明形态的进阶升级,而是成为了一种能够直观反映中国式现代化总体发展历程,并且始终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先进文明样态。
(三)话语载体:繁荣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所关涉的并不只是文明“转型”这一动态表象,还蕴含着进一步探究“以何体现转型”的文明考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5]作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发展着的文化样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受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根脉滋养,具有超越时空的文化魅力和思想意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最鲜亮的文明标识。同样作为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伴而生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生了必然的理论耦合。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如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生关联?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要厘清文明形态与文化样态的辩证关系。一般来说,文明与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基于不同场合会有各自的使用口径,但要将二者进行相对区分仍然是复杂的。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尝试将文明与文化进行细致区分:文化可以理解为“人类生活抽象的样法”,而文明则可以理解为“生活中的器皿”。也就是说,文明比文化具有更加显性的、固定的界限,文明是从文化样态中生成的、更高阶段的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当代呈现,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不可或缺的话语载体,生动彰显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在当下文化语境的话语面相与民族特色。
总的来说,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辩证关系可以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具象体现,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要旗帜鲜明地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两者形成了一种“价值互洽”的协同模式。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只有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载体赋能才能真正摆脱游移不定的抽象状态,而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持续推进又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必要的发展诉求与理论支撑。
二、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内涵要旨
从“中华文明”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话语叙事的进阶展演所表征的并不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明割裂,而是融会贯通、相互成就的文明共生。“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6]“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作为一个原创性的话语概念,其话语生成背后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思想底蕴与文明基因。
(一)理论筑基: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魂脉”指引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马克思主义所描摹的文明发展之路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展开。作为具有鲜明实践性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的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了真理指南。但也应承认,生发于西欧文化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与独具本土特色的中华文明难免存在一定程度的“理论视差”。如何弥合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理论错位”关乎能否有效激活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功能。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合理选取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精粹,确保了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中能够与科学理论保持良性互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7]同样,推进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亦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正向赋能。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须臾离开人类文明演进这一时代主题。对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展开深刻批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命。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重塑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形式。正是因为对资本主义的异军突起有着深切感知,马克思得以更加全面地审视和批判资本主义发展态势及其现代性隐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被资本逻辑宰制的现代化,既能给世界各个民族带来进步的曙光,又裹挟着资本反人性的伤害。与资本逻辑所支配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明形态,归根结底是为资本主义的扩张而服务的,这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语境下的文明发展不可能契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规规律,势必会走上文明演进的“偏斜之路”。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深刻揭示了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也是推进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应始终贯彻的价值标准,只有以“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才能让文明形态的演进正确回应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
(二)思想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8]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不是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的文明产物。中华文明需要在承继传统中得到肯认,也需要在现代实践中换羽新生。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儿女五千多年的劳动智慧,集中反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和思想风貌,是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宝贵财富。只有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才能获得“根脉”滋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具有内在的同构性。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动展现了中国人的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彰显着中华民族鲜明的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并不是对中华文明的“脱轨”和“否定”,其生发机理仍是肇始于中华文明和谐统一、继往开来、和合共生等理念范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禀赋与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现代”指向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实现了完美融合,生成了新的有机文化生命体。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境遇下焕发光彩,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之路的重要命题。面对新时代更加活跃且复杂的文化格局,多元文化相互碰撞、彼此角力,虽然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提供了发展机遇,但同时也要求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中应自觉与不良文化划清界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9]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关键密钥。“守正”在于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血脉与文明基因。“创新”在于推动中华文明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双重更新,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引向深入。
(三)文明互鉴:西方现代优秀文明成果的“对话”交融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不同文明持续交流对话而生成的先进文明形态,既蕴含多元文明的精华缩影,又彰显本国文明的鲜亮底色。“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0]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及时从西方现代优秀文明成果中汲取养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才能更加契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绝不拒斥西方现代优秀文明成果。文明多样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表征,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越频繁,现代社会的发展便越快速。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具有兼容并包的突出特点。无论是大唐盛世的文明壮阔图景,还是郑和下西洋的文明宣介之旅,中华文明始终致力于在和平基础上构建一种兼收并蓄、取长补短的文明交往形式。围绕如何学习和借鉴不同文明进步成果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1]只有坚持和平对话和虚心学习,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才能在风云激荡的世界文明格局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并不是对西方现代优秀文明成果进行简单摄取和全盘吸收。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具有明确的话语主体,它绝不甘于沦为任何文明形态的“傀儡”和“替身”,而是彰显着中华文明自身的文明定力和文化主体性。因此,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所提倡的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高度的原则遵循。不同文明需要在平等对话的架构内开展交流与学习,做到既尊重各自文明的本土特色,又契合文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应积极找寻“自我”与“他者”的发展平衡,勇于吸收西方现代优秀文明成果养分,并对其进行本土调整与合理内化,使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开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世界意义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与人类文明发展嬗变的一般规律深相契合。因此,深入阐释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价值蕴含,不能只沿着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展开探索,而应立足世界文明发展格局综合考量。
(一)重塑发展模式:为打破“西式文明”中心范式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纵深演进的文明形态,与西方现代化相伴而生的“西式文明”有着本质不同。长期以来,西方意识形态极力渲染“现代化=西方化”的文明氛围,企图阻碍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干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客观呈现。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塔尔克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从“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系统”[12]出发来探求经济要素同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关系。他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化过程”进行了补充说明,以“开放界限”为目标讨论经济系统所具备的政治关联性。帕森斯的意图非常明确,那便是确证由西方政治制度所构成的新科层体系造就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合理性”与“进步性”,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决定论进行辩护,试图把“西式文明”确立为人类社会通往现代文明的中心范式。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立足全人类文明的发展高度,深刻揭示了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文明形态的形塑与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而非受制于西方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规制。文明发展只有形态上的区别,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西式文明”只是现代文明的表征之一,并不是人类文明的中心或标准,更不能直接等同于人类文明的全貌。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化解了“西式文明”的“现代性之殇”,为人类社会通往真正的文明彼岸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构建发展空间:为促进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注入了中国力量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在自我塑造过程中彰显出极强的包容性,为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与交融形构了发展空间。回溯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从原始奴隶文明到资本主义文明,人类文明总是在前进性与曲折性交织中向前发展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元主导性”,在意识形态层面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这些论调想要确立资本主义文明的无上权威,从而为资本主义“新殖民”进行有力辩护。然而,文明演进实践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强制压服是违背文明交往规律的。文明交往的生成与发展从来就不是资本主义文明意识形态规训的附属物,而是基于文明发展客观规律的现实需要。福山(Francis Fukuyama)笔下的“历史终结”将现代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及其伴生物经济自由主义的增长”[13]看作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不过是将资本主义看作“自然产物”的幻觉。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驳斥福山的同时本身也具有文明保守主义倾向,将文明冲突的动因归结为“文化认同”,[14]无非是将文明产生的缘由作为阻碍文明交流的诱因。显然,“西式文明”先天的优越性与排他性不利于文明交往,反而会压缩人类文明的交往空间。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建立在深刻透析人类文明递嬗规律之上,切实关照人类文明前进与发展的必然原则,它强调的是“美美与共”的文明共和,而不是谋求“一元文明”的模式再造。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在理论与实践之维实现了人类文明评价范式与发展规律的全新叙事,以文明交互破解了文明隔绝的“意识形态藩篱”,以文明相师穿透了文明冲突的“文化认同障碍”,以文明共存破解了文明优越的“一元主导壁垒”,为拓展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空间注入了中国力量。
(三)创新发展形态: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了中国贡献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多元文明基因协同共育的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5]这一重要论述高度提炼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内涵与具体所指,道明了中国共产党所缔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绝非抽象的“一元文明”,而是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归与社会发展图景的文明创新范式。首先,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为世界文明的深度进阶提供了先在原则。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物质水平高速发展的伟大成就,既充分肯定了生产生活实践对于文明开创的基础性作用,又注重在发展中有效遏制“资本逻辑”的肆意生长。其次,政治文明的丰富完善为世界现代政治文明标立了崭新注脚。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所具有的鲜明的人民立场超越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抽象民主”,实现了人民作为价值主体的真正复归。最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协同发展创造了世界文明现代演进的全新评价范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需要更为广泛的精神向心力,还需要摒弃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模式所固有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两极异化”内在弊端,以多元评价指标客观衡量和定位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从而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平衡、和谐、共享的高层次发展。
综上所述,深入阐释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世界意义关乎世界文明发展格局的正确建构。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逻辑,拓宽了各民主国家实现文明现代化的多样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文明迷思,以其开放包容的文明特性走出了以文明平等、文明交流、文明互鉴为基础的人类现代文明发展新路向,体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文明范式,成功将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至更高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2][3][6][9]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6,3,2,6,11.
[4]布尔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22.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15.
[7]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4.
[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7.
[10]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97.
[1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1.
[12]塔尔克特·潘帕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76.
[13]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8.
[14]于小植.从“文明冲突论”走向“文化冲和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8(01):19-29+218.
[1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83.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及其话语策略研究”(编号23CKS0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宗君】